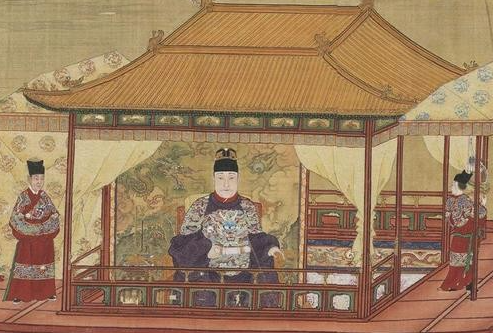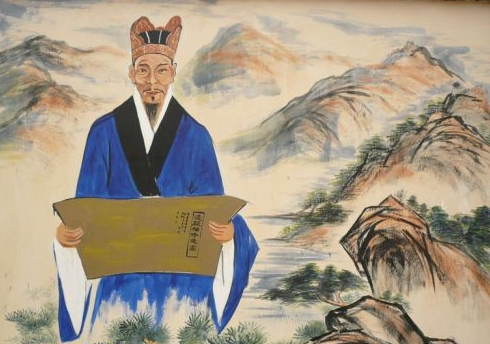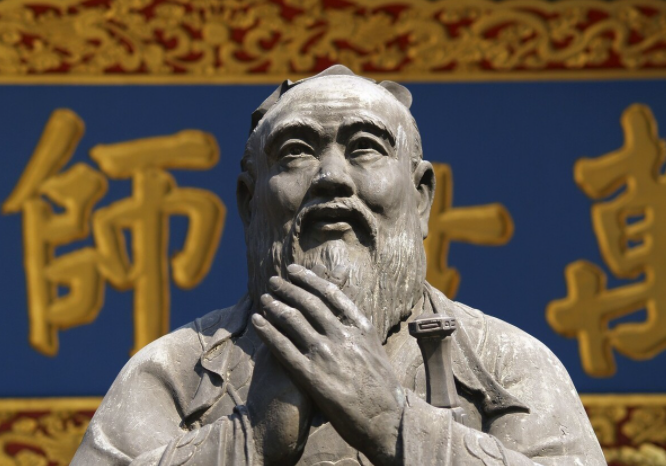明朝萬曆三十年,禮科給事中張問達上疏彈劾李贄,指控他“壯歲為官,晚年削髮,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對社會風氣造成很壞的影響。李贄經常在書中發表不當言論,例如他讚揚竊國盜賊呂不韋和李園為智謀之士;宣稱暴君秦始皇是千古一帝;對於背棄父母而私奔的卓文君,李贄誇她擅長擇偶;而在說到歷事數主的奴才馮道時,李贄又稱讚他是不以利祿縈心的好官。更荒謬的是,李贄竟敢“以孔子之是非為不足據”,真是“狂誕悖戾。”當然,在張問達看來,李贄最可恨的地方在於“肆行不簡”,他與無良之輩遊居尼姑庵,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者,真是傷風敗俗。
最後,張問達說最近李贄將要來通州講學,請求陛下命令通州地方官將其逮捕,發回原籍治罪,此外還需將李贄的著作全部焚毀,以免毒害人心。萬曆帝讀過奏疏後,親自批复說:“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令廠衛,五城嚴拿治罪。其書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盡搜燒毀,不許存留。”
這樣,中國歷史上又一位著名的殉道者出現了。
一場荒唐的文化審判
李贄是福建泉州人,他在青年時參加科舉成為舉人,卻因嫌路途遙遠,不肯進京考進士,只做教諭、郎署之類的官職。
有一天,李贄在路上散步,偶遇一位道學先生。道學先生問他說:“公怖死否?”
李贄答曰:“死矣,安得不怖?”
道學先生便勸他說:“公既怖死,何不學道?學道所以免生死也。”
李贄驚嘆道:“有是哉!”於是從此潛心學道。之後又升任雲南姚安知府,執政期間,法令清簡,不言而治。到了中年,李贄在內心中開始厭惡起官場來,有一天,他逃入雞足山隱居,不肯出來;為此,雲南御史劉維奇只得幫他辦理了退休手續。
李贄不願受到親族的牽累,他乾脆將妻兒全部遣返故鄉,自己則寄居在朋友耿定理的家中,斷俗緣,參求乘理,自稱“流寓客子”。不久之後,耿定理病死,其兄耿定向驅逐了李贄。貧困之下,李贄只得去龍潭湖的維摩庵蓄發出家,日以讀書為事,又來回與耿定向論戰,抨擊假道學。官府以“僧尼宣淫”為藉口,燒毀佛院,李贄被迫流浪各處,最後只得寄住在馬經綸之家。
萬曆帝下令緝拿李贄之時,後者已是七旬老翁了。當時,李贄才剛抱病完成《九正易因》,官兵就來推門抓人。李贄聽見屋外動靜很大,便問馬經綸怎麼回事,答曰“衛士至”;李贄一听就知道這些人是來抓自己的,於是他勉強站起來,大吼:“是為我也。為我取門片來!”說完就躺在門片上,當官兵闖進來後,李贄對他們說:“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說完便被抬走了。
第二天,大金吾坐堂審訊,左右二人將李贄扶入堂下,臥於階上。金吾厲聲恐嚇道:“若何以妄著書?”
李贄抗辯說:“罪人著書甚多,具在,於聖教有益無損!”
金吾笑其倔強,然而終究審不出什麼結果來,只得宣布退堂侯旨,然而等了很久朝廷都沒有下旨說要如何處置這個“異端”。李贄每天都在監獄中閱讀詩書,神態自若。忽然有一天,他對看守的人說自己需要剪頭髮,看守的人見他本來就是個和尚模樣,故而給了他一把剃刀。於是李贄趁看守的人不備,持刀自割咽喉,不料竟未立即死成。兩天之後,見李贄尚未氣絕,看守的人問:“和尚痛否?”
李贄用手指在手掌上寫道:“不痛”。看守的人感到幾分哀傷,嘆道:“和尚何自割?”李贄繼續寫道:“七十老翁何所求!”之後便淒然而逝了。
李贄究竟犯了什麼罪?
在李贄死後,他的書籍被列入禁毀書目。天啟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再度奉旨嚴令“李贄諸書怪誕不經,命巡視衙門焚毀,不許坊間發賣,仍通行禁止。”可見明朝統治者不僅想要從肉體上消滅李贄,而且還要讓他的精神從世間蒸發,不留下一絲痕跡。
然而據顧炎武《日知錄》的記載,李贄的書始終屢禁不絕,一直在民間悄悄傳播,這一方面是因為“士大夫多喜其書,往往收藏,至今未滅。”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的書其實並非政敵所描繪的那樣,是洪水猛獸或大毒草。這些書裡的大部分內容其實都很契合主流價值觀,只是部分地方發揮了李贄個人獨特的想法,不料卻被人當做把柄,拿來大做文章而已。
首先,張問達指控李贄“挾妓女,白晝同浴”,這缺乏依據。李贄的朋友袁中道在《李溫陵傳》中說李贄本人“體素癯,澹於聲色,又癖潔,惡近婦人,故雖無子,不置妾婢。”這說明李贄的身體一直都不怎麼好,而且他年紀已經大了,又有潔癖,不近女色,並不像淫亂之人。
其次,李贄在《答以女人學道為見短書》中說見識有長短之分,卻無男女之別。大部分女子之所以見識較短,那是因為她們所見不出閨閣之外,倘若男女共入學堂學習,女子的能力並不差於男子。所以他不排斥招收女弟子,也很樂意讓女弟子們走出閨閣,到維摩庵來聽自己講學。這種男女平等、開放自由的思想竟被衛道士們描繪成了“勾引士人妻女”,進行百般污衊。
最後,對於“妄著書”的指控,李贄當堂反駁說:“著書甚多,具在,於聖教有益無損!”要求與官府就著這些公開出版的書籍進行辯論,看看它們究竟“妄”在何處。然而,官府終究沒有給他這個機會,在官府看來,李贄首先是可惡,之後才有罪,最終再根據“可惡罪”來在法律條文上找個正規的罪名——而李贄最可惡的地方就在於他違背主流價值觀,“以孔子之是非為不足據”。
李贄對神化孔子現象的反思與批判
在李贄剛死不久,禮部尚書馮琦就上奏說:“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崇正辟邪,甚盛舉也。臣竊惟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鑑》、性理諸書而外,不列於學官,而經書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為準。此即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
萬曆帝批復道:“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可開列條款奏來。”肯定了“獨尊孔氏之旨”的意見,也證實了誅殺李贄的真正原因就在於此。
李贄是一個著述豐富、在文化圈子中影響頗大的人物。他所輯錄的《藏書》和《續藏書》幾乎相當於一部從西周至明朝的通史,其可讀性要高於卷帙浩瀚的《二十一史》與《資治通鑑》;為了配合閱讀,李贄又編了一部《史評綱要》,抒發個人的歷史見解,其觀點新穎,發前人所未發,深受士大夫們的喜愛。此外,李贄還對《西廂》、《水滸》、《西遊》這些藝術性的書籍進行點評,使士大夫們的眼光從枯燥的經書中轉移出來,這些都不利於“獨尊孔氏之旨”。當然,李贄最大的可惡之處是在《焚書》與《續焚書》裡對“獨尊孔氏之旨”這一祖宗立教進行了直接的抨擊。
在《題孔子像於芝佛院》中,李贄說世人之所以認為孔子是大聖人,佛老二教是異端,這不過是嚴父塾師進行教育灌輸的結果罷了;而嚴父塾師也並不知道為什麼孔子是聖人而佛老是異端,他們只是尊奉先儒傳下來的教條而已。然而這些教條還都是歪曲過了的——孔子自己明明說過“聖則吾不能”,何以硬要尊其為聖人?孔子活著的時候佛教尚未傳入、道教尚未建立,哪裡能知道他所說的“攻乎異端”是指佛老?因此,以孔子為聖人、以佛老為異端,不過是儒者們自己臆測出來的結論,然後再通過沿襲而誦,漸成千年一律的教條了,這實在是“強不知以為知。”儒者們既然以孔子的信徒自居,那麼就應該相信孔子說過的話;孔子承認自己不是聖人,說明他也不是全知全能的,所以不能“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這是最清晰的邏輯,也是最簡單的道理。
在《答耿中丞》裡,李贄說孔子從未叫別人都要來學習他本人,他常說“為仁由己”、“古之學者為己”、“君子求諸己”,何曾說過“求之於夫子”?學問思辨、追求真理主要還是靠自己,老師只是一個路標、一根手杖,只能給你指出個大致方向。哪裡有人蠢到要把自己的老師神化成十全十美的聖人,然後再用他的思想來代替自己的思想,把他的理論塞滿自己的大腦?一切表達、證明、著作,其目的不在於俘虜別人,使別人成為自己的思想奴隸,而是為了引起別人的認識活動,喚醒他們自身所擁有的理想。
儒者們之所以相信孔子,並不是因為真理寄存在了他的大腦之中,而是因為他的語言文字能引發我們的思想,說出了我們的理智,僅此而已。不要學習孔子的思想,而是要學習他的方法,孔子的方法就是“君子求諸己”,發揮你的理智,獨立思考。當今的蠢材們偏要尊奉孔子為祖師爺,“獨尊孔氏之旨”,卻又對孔子的思想學得四不像,結果不過是用自己的謬見來壓迫各種獨立的思考罷了。
正因為李贄的這種頗具啟蒙意識的思想和言論戳痛了明朝統治者和衛道士們的弱點,所以他才遭到了圍攻,並且在不公正的審判中,淒涼的死在監獄裡,在明清兩代都遭受罵名。然而,正如顧炎武所承認:“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人者,莫甚於李贄,然雖奉嚴旨,而其書之行於人間自若也。”或許,老百姓的志趣與“聖人之徒”們早就貌合神離了,要么李贄的書怎麼會屢禁不絕呢?